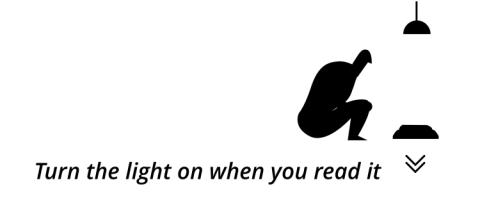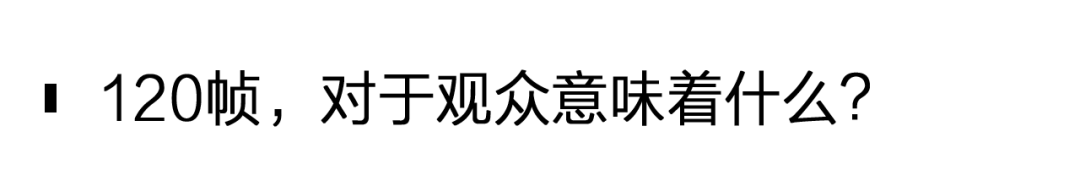
这对片方和李安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文字永远无法直接描述它带来的实际体验。李安用120帧的规格制作的电影《双子杀手》,目的是为了一种在视觉上极致的流畅,效果呢……很遗憾,就是大部分观众对此无感。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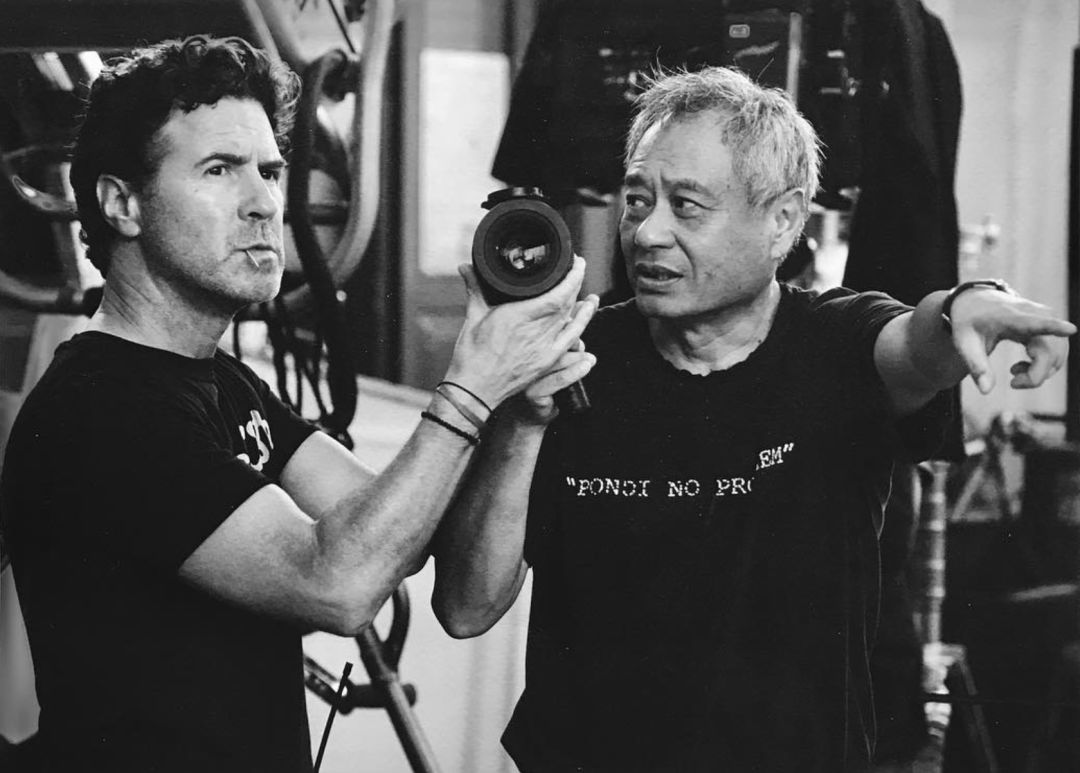
《双子杀手》最大的看点和争议,都是来自 “120帧”。百年电影史,绝大多数影片都是用24帧拍摄的——银幕上每秒钟更新24帧画面,人眼看起来就是连贯动态的影像,“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我们学24格学了一辈子,从来没问过为什么是24格。它其实就是片商给出的最便宜就能连起来看的格式,没有什么科学道理。而艺术家一直被这个低限度框在里面,创作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四年前用120帧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李安说:“我已经看到了更清晰的电影,就不能假装从来没看过。” 《双子杀手》公映版本也有好几种不同的格式。从技术上讲,从24帧到120帧,电影工业的一次飞跃,但这种技术革命落实到观影体验究竟有多大提升?真能把观众“震住”吗?我先看了120帧、4K、3D的最高规格《双子杀手》,第二天又去看了场24帧、2K、2D的“低配版”。感受很复杂,直接上结论:这根本就是两部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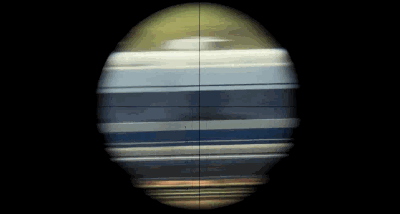
24帧画面下,列车飞驰而过,留下的只是一条条模糊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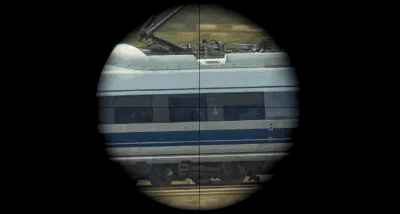
120帧画面下,连车上乘客都能看的清楚虽不到天壤之别的程度,但是当我分别看完120帧和24帧两版《双子杀手》,回想起来,我观影时的关注点分别被带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看视效,我被震得目瞪口呆,脑海里分分秒秒都在想“这是啥啊咋回事呢怎么弄出来的玩意”;后者看故事,我有点犯困,感觉平淡如水,即使是李安一贯的细腻哲思,这故事也已经落后于时代。
在对新技术的探索运用上,李安远远走在了时代之前,而他为此不得不做了故事性、艺术性上的妥协——是的,他是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奈之下的妥协。李安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请大家担待,这次我往后退了一步”,相信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曾经两次捧起小金人的世界级导演会不懂讲好故事?我来告诉你,为了把电影技术往前推这一大步,李安做了怎样的妥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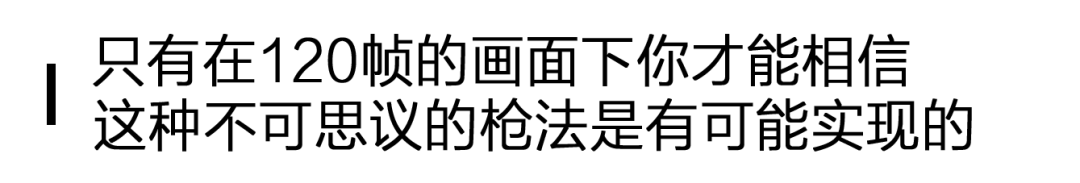
120帧的技术革命,颠覆了以往电影制作的视觉规范,让万物在银幕上呈现出前所未见的面貌。 影片开头,威尔·史密斯饰演的老杀手在执行任务,需要在两公里开外狙击坐在一列高速行驶列车中的目标。狙击手远距离打移动靶,在很多战争片和动作片里都有过类似的情节,这不新鲜,不论其现实合理性,反正我们知道主角一定是神枪手,一定会打中。
但是有没有120帧,这镜头看起来差别可大了——在120帧的极致流畅的画面里,高速行驶的列车和坐在车窗边的目标人物,即使在镜头前一晃而过,看起来依然是清晰的,没有虚影。而普通24帧的画面,那就是风驰电掣呼啸而过,啥都没看清就晃过去了。所以在120帧版本里我甚至看明白了一个狙击手要想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命中目标,他的射击动作原理:前半秒的准星锁定目标人物头部,后半秒是迅猛地甩了一下枪,让准星朝列车前进方向快速平移一段距离然后击发。子弹穿过车窗玻璃,打进了目标人物的脖子,任务完成。
只有在120帧的画面下,你才能看清楚狙击手这一枪是怎么打的,你才能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枪法是人类有可能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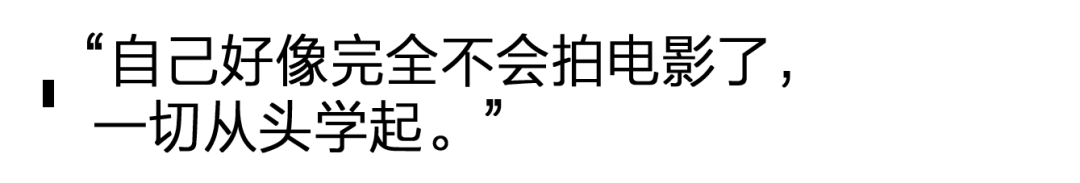
由于上述万物清晰可见的效果,演员的表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 李安自己说的,说从《比利林恩》到《双子杀手》,自己好像完全不会拍电影了,一切从头学起,120帧4K加上3D的画面,在拍摄时的布光、景深等等细节参数全都变了。他在片场反复试错,拍了几个月才找到正确的感觉。这种“正确”的感觉,让观众仿佛在现场看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特写镜头下,威尔史密斯脸上的毛孔都能看的清清楚楚,嘴角的微微抽搐、眼眶里泪水的流淌形态都一览无遗。有人说看120帧反而容易“出戏”,在这种视觉效果下,观众有可能被某些非常细微的画面细节带走注意力,而这些细节通常是被忽略的。
120帧对演员的要求同样极高。一方面要在细节上做到极简,所有演员都必须素颜上阵,因为化妆就会让观众忍不住去看你脸上的粉底颗粒或是眉笔的画痕;另一方面在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上又要到位,经受得住“极限真实感”的考验。

在演员的选择上,其实没有太多选择:“要找一个有很高知名度的动作演员,从20年前一直红到现在,而且现在还能打,也就是汤姆·克鲁斯和威尔·史密斯了。”阿汤哥没档期,史皇很高兴接下了这部戏,但李安对他说:“你先来看一看我要怎么拍,你如果吓着了,不愿意的话,回头还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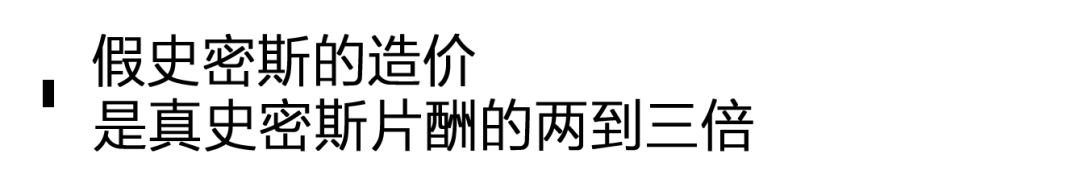
李安做的极限技术实验,除了探索万物和真人在全新视觉环境中的表现,他还想试试“假人”能不能骗过观众的眼睛。 威尔·史密斯今年51岁了。《双子杀手》同时呈现了他如今饱经沧桑的面容和20岁左右小伙子的脸,两张脸都同样真实可信。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老的那个是威尔·史密斯真人,年轻小伙子那个完全是数码技术的产物,是个彻底的“假人”。好莱坞的特效有多先进不用说,过去无数常规影片里以假乱真的镜头我们也看多了。
但李安想的是,既然120帧让真人脸上的毛孔都能看清楚,演员演得对不对、好不好一目了然,那么“假人”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吗?这个念头把特效公司折腾惨了,120帧的特效镜头工作量是普通24帧电影的五倍,这意味着庞大工作量和不菲的预算,据称假史密斯的造价是真史密斯片酬的两到三倍。
李安的视觉实验仍然成功了。当真假史密斯在120帧的大银幕上同框时,我非常努力瞪大眼睛想要找破绽,想要找出真人假人的哪怕一丁点“肉感”和光影的差别——但我失败了。

如果真人演员都不再成为必需,未来的电影将会变成什么样?李安把这个问题摆在了电影人面前。 为了摆出这个问题,他选择了一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流转的剧本,一个关于克隆人的故事。时隔二十多年,“克隆人”的热度已经消散,故事本身对于克隆人伦理、情感关系的探讨,也只是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
《双子杀手》是按照好莱坞工业流程完成的类型片,以李安的造诣和地位,类型片对他来说其实毫无挑战性。这个剧本能够搬上银幕,只是因为它能满足李安对电影的技术探索的要求,由此对行业未来提出一种技术上的可能性。

在这样一部充满极客探索精神的电影面前,还有没有必要去思考故事性、艺术性、哲学性,或者这个性那个性?我们还能如之前一样,继续期待如今已经变成技术拓荒者的李安吗? 我的答案是可以。
120帧画面确实震撼,李安仍然是令人崇敬的华人之光。电影行业如果少了李安这样的探索者,动作电影的视效会不会继续重复无聊的套路?《双子杀手》120帧版一张票200块钱,在影院里目瞪口呆两小时,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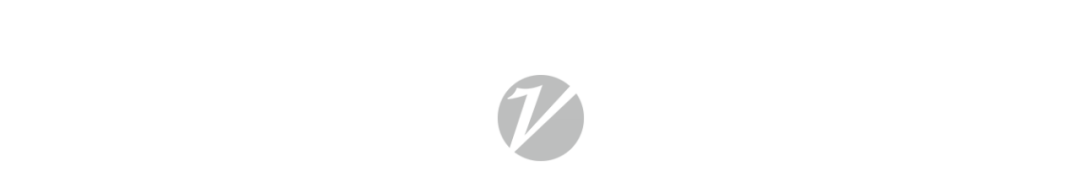
文:武云溥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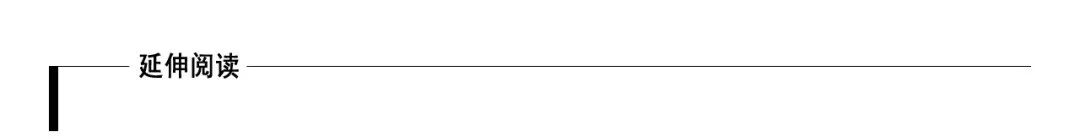
父亲永远坐在李安的心里 / 文 何松岭
李安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家待业了六年,最后靠《推手》跟《喜宴》的剧本获奖才走出谷底,这两部电影属于李安的所谓“父亲三部曲”,父子间的矛盾是突出看点,李安拍得极为精彩,将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特别是父亲的隐忍,拿捏得非常准确,拿奖是实至名归。
李安的父亲是中学校长,思想保守,李安出生时,父亲冲口而出的是“李家终于有后了”。给长子取名一个“安”字,也有纪念老家江西德安的意思。父亲对这个长子从小期望极高,高中时李安一个星期补十堂课,补课老师全是名师,他的学习成绩却没有起色,高考两次全都落榜,最后只好去考了艺专。
艺专的宿舍住六个人,只有两张桌子,老鼠大白天到处乱窜。长子在读这样的学校,专业又是影剧科,父亲感到面上无光,于是长子教育状况一度是访客来李家拜访聊天的禁忌话题,若谁不知趣地提到,空气中便会充满可怕的沉默。
饶是如此,父亲似乎对李安有着无限的耐心和绵绵不尽的支持。当他读艺专时,羡慕同学有超八厘米摄像机拍短片,父亲就买了一部送给他,李安收到礼物时内心狂喜,正是用这部摄像机,他拍出了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后来利用此片申请到伊利诺伊大学留学的机会。
李安的父亲不但支持他到美国读戏剧本科,也支持他到纽约大学读电影制作的研究生,毕业后赋闲在家的六年里,还补贴远在美国的李安家用。儿子跟林嘉惠结婚的时候,父亲从台南飞到美国来参加,看到婚礼是所谓公证结婚,不像传统的中式婚礼那么热闹,场面也很是冷清。在台湾社会地位颇高的父亲,万万没想到长子的婚礼竟是这样的场面,内心非常难过。
在家里待业六年之后,李安在制作他的走出谷底之作《推手》时,每天花十一个小时剪片,来回开车也要两个小时。当时正值暑假,李安每天工作结束回家,父亲都跟母亲在家门口等着他进门。
李安的父亲一方面对儿子终于开工充满期待,一方面还是希望李安放弃拍电影,子承父业,回台湾进入教育界。在李安把简·奥斯汀的名著《理智与情感》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后,父亲还对李安说:“小安,等你拍到五十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你就退休教书吧”,父亲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儿子李安四十一岁。
就在那之后五年,四十六岁的李安凭借《卧虎藏龙》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把小金人带回台湾,家门口挤满了媒体记者与左邻右舍。他还给母校台南一中捐了一百万元奖金,身为一中老校长,父亲原本已备受尊敬,李安的衣锦还乡,让父亲更感增光。
当父亲在采访中谈到儿子的职业选择时,他说:“我就像《喜宴》里最后一幕高举双手的老父”,劝退不得,就开始扮演鼓励者的角色。李安拍《绿巨人》时筋疲力尽,陷入瓶颈期,跟父亲说不想再拍电影,父亲却鼓励他,“你还不到五十岁,只能带上钢盔继续往前冲,不做电影,你要做什么?你会很沮丧。”父亲还写了一幅字给他:“入山不必太深,下笔不必太浓”。李安接着就拍出了《断背山》,正是这部电影为他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父亲在《断背山》拍摄期间病逝。
于是在电影创作中,李安擅长讲父亲,也就不足为奇。《推手》里的老朱,退休后从北京去美国跟儿子生活,洋媳妇是作家,天天在家写小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面对面朝夕相处,矛盾爆发成为必然。儿子夹在中间,无奈得拿脑袋撞墙。在《喜宴》里,同性恋儿子受不了父母催婚,于是假结婚希望以此结束无尽的催逼。儿子、情人和假媳妇的各种演戏,父亲看在眼里,却不点破,配合着参加了婚礼和喜宴。《饮食男女》里的老朱身为大酒店的退休大厨,每周在家操办一桌盛宴来维系跟三个女儿的感情。这些都是两代相处的哲学,《双子杀手》里的亨利,面对奉命来追杀自己的克隆人,复杂的情绪里自然也有类似血脉传承或反抗的意味。在无穷的情感矛盾处理中,李安是迄今探究得最多也最深的导演,说他为了技术而全然放弃了故事和情感,倒不如说他是不愿陷入好莱坞的剧情俗套。抑或让观众聚焦更多的注意力在大荧幕上,纵使落得“不再会讲故事”的差评,也是一件值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