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释字号:释字第469号
解释争点: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请求赔偿,以被害人对公务员之特定职务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而怠于执行为限之判例,是否违宪?
解释日期:民国87年11月20日
解释文法律规定之内容非仅属授予国家机关推行公共事务之权限,而其目的係为保护人民生命、身体及财产等法益,且法律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事项规定明确,该管机关公务员依此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所负作为义务已无不作为之裁量馀地,犹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被害人得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谓:「”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所谓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係指公务员对于被害人有应执行之职务而怠于执行者而言。换言之,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始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若公务员对于职务之执行,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之行为者,纵公务员怠于执行该职务,人民尚无公法上请求权可资行使,以资保护其利益,自不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对于符合一定要件,而有公法上请求权,经由法定程序请求公务员作为而怠于执行职务者,自有其适用,惟与首开意旨不符部分,则係对人民请求国家赔偿增列法律所无之限制,有违”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意旨,应不予援用。
理由书”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人民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係对国家损害赔偿义务所作原则性之揭示,立法机关应本此意旨对国家责任制定适当之法律,且在法律规范之前提下,行政机关并得因职能扩大,为因应伴随高度工业化或过度开发而产生对环境或卫生等之危害,以及科技设施所引发之危险,而採取危险防止或危险管理之措施,以增进国民生活之安全保障。倘国家责任成立之要件,从法律规定中已堪认定,则适用法律时不应限缩解释,以免人民依法应享有之权利无从实现。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亦同」,凡公务员职务上之行为符合:行使公权力、有故意或过失、行为违法、特定人自由或权利所受损害与违法行为间具相当因果关係之要件,而非纯属天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被害人即得分就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依上开法条前段或后段请求国家赔偿,该条规定之意旨甚为明显,并不以被害人对于公务员怠于执行之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为必要。
惟法律之种类繁多,其规范之目的亦各有不同,有仅属赋予主管机关推行公共事务之权限者,亦有赋予主管机关作为或不作为之裁量权限者,对于上述各类法律之规定,该管机关之公务员纵有怠于执行职务之行为,或尚难认为人民之权利因而遭受直接之损害,或性质上仍属适当与否之行政裁量问题,既未达违法之程度,亦无在个别事件中因各种情况之考量,例如:斟酌人民权益所受侵害之危险迫切程度、公务员对于损害之发生是否可得预见、侵害之防止是否须仰赖公权力之行使始可达成目的而非个人之努力可能避免等因素,已致无可裁量之情事者,自无成立国家赔偿之馀地。倘法律规范之目的係为保障人民生命、身体及财产等法益,且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事项规定明确,该管机关公务员依此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负有作为义务已无不作为之裁量空间,犹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或拒不为职务上应为之行为,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被害人自得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至前开法律规范保障目的之探求,应就具体个案而定,如法律明确规定特定人得享有权利,或对符合法定条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向行政主体或国家机关为一定作为之请求权者,其规范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益,固无疑义;如法律虽係为公共利益或一般国民福祉而设之规定,但就法律之整体结构、适用对象、所欲产生之规范效果及社会发展因素等综合判断,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时,则个人主张其权益因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而受损害者,即应许其依法请求救济。”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所谓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係指公务员对于被害人有应执行之职务而怠于执行者而言。换言之,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始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若公务员对于职务之执行,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之行为者,纵公务员怠于执行该职务,人民尚无公法上请求权可资行使,以资保护其利益,自不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对于符合一定要件,而有公法上请求权,经由法定程序请求公务员作为而怠于执行职务者,自有其适用,惟与前开意旨不符部分,则係对人民请求国家赔偿增列法律所无之限制,有违”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意旨,应不予援用。
依上述意旨应负赔偿义务之机关,对故意或重大过失之公务员,自得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项行使求偿权,如就损害赔偿有应负责任之人时,赔偿义务机关对之亦有求偿权,乃属当然。
大法官会议 主席 施启扬
大法官 翁岳生
刘铁铮
吴 庚
王和雄
王泽鑑
林永谋
施文森
孙森焱
陈计男
曾华松
董翔飞
杨慧英
戴东雄
苏俊雄
不同意见书大法官 孙森焱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前段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准此,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须公务员为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行为,因故意或过失逾越权限、滥用职权或违背对于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为要件。所谓执行职务之行为,包括作为及不作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以作为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而符合上开规定之要件者,国家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若以不作为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则须公务员依法有作为之义务为要件。按国家行使统治权,依法律之规定有课公务员作为之义务,以增进公共利益者,亦有以保护第三人之权益为目的者。公务员之作为义务如係专为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则其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行为,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亦不能因公务员不执行该作为,即认为人民之权利因而遭受直接之损害,自不得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又公务员之作为义务除为增进公共利益外,兼有保护第三人之权益为目的者,尚须视有无赋予公务员就作为或不作为,为裁量之权限,以定国家之损害赔偿责任。关于裁量权之行使问题,除法律对主管机关应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之事项,定有明确规定外,并应斟酌人民自由或权利,因行政不作为所受侵害之危险程度、因行政作为得防止侵害权益之可能性、公务员对于损害之发生是否可得预见、侵害之防止是否须仰赖公权力之行使始可达成目的等因素,于公务员就作为或不作为已无裁量馀地时,因其故意或过失而不作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致生损害,则国家即应依上开规定负赔偿责任。类此情形,与公务员以作为加害人民之权益者,应由国家负赔偿责任,并无二致。至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规定:「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亦同。」其立法意旨係指依法律明确规定,第三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该请求权因不能实现或因迟延执行,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之情形而言。关此公法上请求权之行使,自行政诉讼法修正实施后,权利人得依同法第五条及第八条规定请求国家机关给付,是与公务员对于规制权限之不作为,具有裁量馀地者,性质有异;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前段规定,人民之自由或权利因公务员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之侵权行为而发生之损害,由国家负赔偿责任者,亦属不同。”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谓:「”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所谓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係指公务员对于被害人有应执行之职务而怠于执行者而言。换言之,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始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若公务员对于职务之执行,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之行为者,纵公务员怠于执行该职务,人民尚无公法上请求权可资行使,以资保护其利益,自不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係专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之规定而为阐释,并未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与”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并无违背。本件多数意见通过之解释文初则谓公务员依法律规定对可得特定之人所负之作为义务已无不作为之裁量馀地,犹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被害人得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向国家请求赔偿;继则谓”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意旨与首开意旨不符部分係对人民请求国家赔偿增列法律所无之限制云云,认有违”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意旨。惟查公务员依法有作为义务者,既云须因「故意或过失」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国家始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其立论基础亦係以”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前段规定之要件为衡酌之依据。盖若适用同条项后段规定,则公务员有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之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之情形,被害人即得请求国家赔偿。如果国家抗辩公务员所以怠于执行职务係因不可归责之事由所致,则应由其负举证责任。可见适用同条项前段或后段之规定,其构成要件及法律上效果,仍属有别。本件解释以前段规定之要件适用于后段规定之公务员侵权行为,混淆二者之构成要件。按依”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国家损害赔偿,除依本法规定外,适用民法规定。」故公务员为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而以积极之作为,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例如公务员对人民施暴之情形,被害人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请求给付慰抚金,以赔偿非财产上损害。对照以观,公务员若出于消极之不作为,以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例如执勤之警察目睹加害人施暴力于被害人,竟袖手旁观而未加制止(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参照),苟具备故意或过失之要件,且按其情节警察已无不作为之裁量馀地,被害人就其所受身体上损害,亦非不得请求国家给付慰抚金。是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不论其行为係作为或不作为,苟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之内容并无二致。由此观之,公务员之侵权行为类型,以上两者应属相同。次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规定以言,”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阐述其立法意旨,係指依法律明确规定,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之情形而言。顾人民之此项请求权有基于财产权,亦有本于人格权性质者,纵因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致受侵害,按其情节,被害人尚无请求赔偿非财产上损害之馀地。例如请求地政机关办理不动产物权之登记事项,经公务员违法驳回登记之申请者,被害人不得请求给付慰抚金,以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始得请求给付慰抚金;如因登记错误、遗漏或虚伪致受损害者,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地政机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又如人民请求户政机关办理户籍登记而遭拒绝者,就公务员因迟延执行职务所受财产上损害,固得请求国家赔偿,至于被害人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法律并无特别规定得请求赔偿。再就主观的责任原因言,国家如抗辩公务员之怠于执行职务係因不可归责于公务员之事由所致,即应就此负举证责任,已如前述。与适用同条项前段时,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係因故意或过失所致者,应负举证责任,尚属有间。此外,公务员若因可归责于己之事由,致迟延执行职务,则依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项前段规定,国家对于被害人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损害,仍应负责。是与适用同条项前段规定时,国家应就公务员所为故意或过失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负责者,又有不同。综上以观,”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前段与后段所定国家损害赔偿责任之规范内容各有所指,公务员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之违法行为,各该规定适用之类型迥不相同。”最高法院”上开判例係专就后段规定之情形而为阐释,与前段之规定无涉。本件多数意见通过之解释,徒依条文表面之文义而为解释,认「被害人得分就积极作为或消极不作为,依上开法条前段或后段,请求国家赔偿」,执以指摘”最高法院”上开判例所述,限缩后段规定适用之范围,有违”宪法”保障人民权利之意旨云云,立论未免率断,难昭折服。按”最高法院”职掌民、刑事诉讼案件之终审裁判,其受理具体诉讼事件,係以第二审判决确定之事实为判决基础。裁判上适用法律乃经由诉讼程序,使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化、明确化、正确化。从而法律规定有不明确者,以解释方式阐明其含义;在法律规定有欠缺时,以补充方式填补其阙漏,使法律的适用完备无缺。判决之见解具有创新意义者,则採为判例,赋予拘束法院之效力。因此,关于判例所採法律见解,除有明显违背”宪法”保护人民权利意旨之情形外,不应因对条文为相异之解释,执判例文义之一端,指为牴触”宪法”之规定,置判例所欲阐述之精义于不顾。斯为尊重最高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职权所当为,本件多数意见捨此而不由,爰提出不同意见书如上。
抄薛○宣等二十二人声请书
兹依”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声请解释”宪法”,并将有关事项叙明如左。一、声请解释”宪法”之目的声请人等因请求国家赔偿事件,受”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八一号判决驳回所请确定。该号判决援引作为裁判依据之同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业已逾越”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文义范围而达于司法造法之层次,究其内容则已实质地侵害、限制了声请人等由”宪法”第十六条所保障之诉讼权及”宪法”第二十四条所保障之国家赔偿请求权,但却无立法者之任何授权,实已牴触”宪法”第二十三条所要求:「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的法律保留原则。为落实”宪法”及”国家赔偿法”充分保障人民权利之法旨,并确保整体法秩序之合宪性,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声请大院解释前揭判例违宪而宣告其不再援用。二、疑义之性质与经过及涉及之”宪法”条文(一)疑义之性质与经过声请人等为台湾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壳○公司」)员工及眷属之亲人,民国(下同)七十九年间,壳○公司为举办员工旅游活动与亚联旅行社订立旅行合约,由亚联旅行社为壳○公司员工及眷属承办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两天一夜「日月潭之旅」旅游活动。然前开旅游所在地之南投县政府就其所管理之日月潭风景区未尽管理责任,不但怠于其取缔违法之职务,任由未经检验合格、救生设备严重欠缺之无照「兴业号」游艇于日月潭风景区内公然载客经营游湖业务,甚且违规于夜间航行;未依法于日月潭风景区设置任何救难机构及医疗急救设施,致声请人等之亲人于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夜间于在日月潭搭乘「兴业号」游艇翻覆,罹难者计五十八人。声请人等前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请求南投县政府赔偿殡葬费、扶养费及精神慰藉金等损害(附件二),惟南投县政府分别于八十年十月三日及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八○)投府诉字第一二○一一八号、(八○)投府秘法字第一四○七三四号函拒绝赔偿(附件三、四)。声请人等乃依法向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对南投县政府提起诉讼,经台湾台中地方法院以八十一年度国字第一号判决(附件五)驳回声请人等之请求后,声请人等依法向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起上诉,亦遭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八十一年度上国字第四号判决(附件六)驳回声请人等之上诉。声请人再向”最高法院”提起第三审上诉,该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八一号确定判决(附件七),则援引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谓「惟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所谓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係指公务员对于被害人有应执行之职务而怠于执行者而言,换言之,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始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若公务员对于职务之执行,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之行为者,纵公务员怠于执行该职务,人民尚无公法上请求权可资行使,以资保护其利益,自不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参阅”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本件被上诉人未于所属日月潭风景区内设置救生医疗机构与设施,乃属公共职务之执行问题。上诉人尚无请求被上诉人为该特定职务执行之公法上之请求权。被上诉人未依法尽取缔无照之兴业号游艇营业,致该游艇违规夜间游湖发生船难,依观光地区游乐设施安全检查办法第四条、第十五条,小船管理规则第三条,南投县日月潭游艇业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被上诉人所属有关单位及游艇业公会所组成日月潭违规小船专案小组虽有取缔无照游艇违规营业之义务,惟该项义务乃专在增进或保护公共安全,虽个人(游客)因该作为亦获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行为,揆诸前开判例,上诉人等不能因被上诉人所属公务员怠于执行取缔无照兴业号游艇违规营业之职务,使其亲人李○珠等五十五人乘船翻覆死亡受损害而请求被上诉人负国家赔偿责任」等语云云,驳回声请人等之上诉。按”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八一号判决据以驳回声请人等所提上诉之该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牴触”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之法律保留原则而侵害声请人等受”宪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所保障之诉讼权和国家赔偿请求权,亦即广义的权利保护请求权。(二)涉及之”宪法”条文:(1)”宪法”第十六条(2)”宪法”第二十四条(3)”宪法”第二十三条三、声请解释”宪法”之理由及声请人对本案所持之立场与见解(一)”最高法院”之判例可为释宪程序之标的按”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虽仅规定「确定终局裁判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发生牴触”宪法”之疑义者」,受裁判之人民得因”宪法”上所保障之权利受侵害而声请解释”宪法”,并未明文提及判例。惟依”司法院”释字第一五四号解释之理由书,可知该条规定所指之确定裁判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乃指确定终局裁判作为裁判依据之法律或命令或相当于法律或命令者而言。”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之判例,在未变更前有其拘束力可资为法院裁判之依据,如有违宪情形,仍应受”司法院”大法官之审查而得为释宪程序之标的,合先陈明。(二)”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一八八一号判决所据为裁判基础之同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侵犯声请人等由”宪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所保障之诉讼权及国家赔偿请求权,致生有无牴触”宪法”之疑义:1”宪法”第十六条及第二十四条係保障人民于其一切自由或权利遭受侵害时,有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请求救济之权利保护请求权:(1)按现代法治国之基本设计,乃以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为其基本架构,并以法(”宪法”为其中最根本者)为各个国家权力之运作规则,此即所谓权力分立和依法而治(ruleoflaw)原则,其根本目的即在于藉此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并使其运作具有预测可能性,以便能终局地确保人民的自由、权利不受国家侵害。于此一权力分立的设计中,行政及立法两权具有主动积极的性格而成为人民自由权利之潜在威胁,而司法权则被赋与制衡、防止行政、立法滥权而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任务,至其手段则是透过人民主动提起诉讼而撤废行政、立法之违宪违法措施,然其本身仍须依法审判,自不待言。(2)是以现代法治国对于人民自由权利之保障,主要係透过司法权的运作而落实,易言之,在法治国理念中,人民权利之守护神实际上係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在实体法上人民有多少权利和自由,于诉讼上便应相应地给予多少救济途径,这就是所谓的「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救济斯为权利」(Ubijus,ibir-emedium;Ubiremedium,ibijus)之法理。此一法理的落实,反应在客观制度面上的,便是「权利的程序保障」(Verfa-hrensgarantie)概念(参”司法院”释字第三九六号解释之说明),在主观上相对的则给予每个人民在其实体上之自由权利受到他力侵害时,得在组织公正的法院下藉由正当的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寻求救济的权利,亦即「概括的权利保护请求权」。无此一程序上的基本权利,则任凭”宪法”的权利清单(billofrights)胪列再多的实体权利,亦属无济于事,易言之,程序权乃具体实现实体权之前提。我国”宪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有诉愿及诉讼之权利,此一”宪法”上明文之争讼基本权利唯有在上述法治国理念的脉胳下,方能清楚的显现其权利内容或描划出其保护领域(Schutzbereich)。申言之,受到国家以外之其他私人的不法侵害时,人民固然得在普通法院提起民刑诉讼请求司法上的救济,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作为对人民自由权利之最大的潜在威胁者-国家时,人民得以行政争讼、国赔诉讼,甚至是声请释宪来排除或防止其侵害。此乃目前人权保障之主流方式,除各法制先进国家之”宪法”外,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昭示所有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独立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开公正的审讯,以确定其权利义务,并判断任何对其提出之刑事指控,也是本于此旨。我国”宪法”以保障人权为本,合乎世界潮流,解释上自难有别于各国立法例。(3)就行政争讼及国赔诉讼之关係而言,二者功能不同,前者用以除去不法侵害人民的行政措施,后者则用以填补因该措施所造成之实质损害,但目的最终则是协力使人民的自由权利回复被侵害前的圆满状态。”宪法”第二十四条虽规定人民于公务员违法侵害其自由或权利时,有请求国家赔偿之权利,但此一权利实已包含于”宪法”第十六条之广义的权利保护请求权中,纵无”宪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仍不得谓人民无此权利。易言之,”宪法”第二十四条係”宪法”第十六条之例示性规定,其解释上重点应置于条文内之”国家赔偿法”立法的”宪法”委託(Verfassungsauftrag),而不能谓人民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已尽于此,否则不啻使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条之规定失去”宪法”上之依据。就比较法的观察而言,德国基本法并未就人民因遭受公权力违法行使致生损害时特别规定其有国家赔偿请求权,但基本法第十九条第四项已规定任何人在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时,必有向法院请求保护之途径。其学说及实务均认为从此项概括之法院保护请求权,当然可以导出受害人民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在”宪法”上的依据,亦足资参考。2”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业已侵害了声请人等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保护请求权:由前述说明可知,所有实体上的权利莫不以可争讼性作为落实的前提。为达此一目的,在有权利必有救济之原则的指导下,提起司法争讼便只能以实体上的权利受侵害作为前提条件,亦即以实体上权利受侵害之主张作为原告起诉是否具备诉之利益而有当事人适格之判断标准,并以此为诉讼能否成立之要件,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宪法”上可资允许的诉讼上条件,否则势将对人民的权利保护构成”宪法”所不允许的限制。此于民事诉讼如此,于行政争讼及国家赔偿诉讼亦然。(3)”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谓:「”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所谓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係指公务员对于被害人有应执行之职务而怠于执行者而言。换言之,被害人对于公务员为特定之职务行为,有公法上请求权存在,经请求其执行而怠于执行,致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始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若公务员对于职务之执行,虽可使一般人民享有反射利益,人民对于公务员仍不得请求为该职务之行为者,纵公务员怠于执行该职务,人民尚无公法上请求权可资行使,以资保护其利益,自不得依上开规定请求国家赔偿损害」。综观要旨,可知该号判例纯係以公权利及反射利益之区别作为其立论基础。按,此一区别源于上个世纪之德国行政法学中的公权利(oeffentlicheRechte)理论,其以(a)国家及其他公法人等行政主体依公法法规之规定负有行为义务(Vehal-tenspflichten);该公法法规并非仅以实现公益为目的,亦具有保护私人利益的目的;该法规所保护之个人,有依该法规所赋与之「法之力」要求行政主体履行其依该法规所负担之行为义务,作为判断个别人民有无公权利之标准,此一标准又称为保护规范理论(Schutznormtheorie)或保护目的理论(Sch-utz-zwecktheorie)。该理论之提出乃是因为在上个世纪的德国法制上,并无任何类似英美”宪法”上的人民可资对抗国家的基本权利的概念,故只好藉由对实证行政法规之解释而建立人民在法制上与国家或君主抗衡之地位,易言之,公权利理论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其功能乃是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下将人民从纯粹的统治客体部分提昇为独立的权利主体或法律主体,因此该理论之用意不能不谓良善。然而,今日我国的”宪法”早已明文将人民的基本权利列为专章,其中列举之各种基本权利条款既是客观有效之法规范(而非”宪法”委託或方针条款),也是主观上可资行使的公权利,这点在我国目前之实务及学说上亦无异议,因此于我国公法实务上,公权利理论有无过分重视或强调的必要,毋宁是值得检讨的,详言之:(a)在目前的行政法实务上,公权利的概念实际上主要是在判断人民提起行政争讼者有无原告适格时,发挥过滤的作用。就诉讼乃权利保护之主要手段,并且诉讼的提起意谓全民共享之司法资源的使用而言,只许权利受有损害之人享有诉权(Klagebefugnis)而可争讼,可以防止滥诉或民众诉讼(Popularklage),自属合理。(b)相对于行政争讼之目的在于除去对人民造成损害之违法行政处分而言,国家赔赔偿诉讼则以填补该违法行政处分所造成之损害为目的。国家赔偿诉讼之提起固与行政争讼相同,须以原告具有诉权而具备原告适格为必要,但除此之外,由于国家赔偿诉讼乃是当人民权利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时的最后一道救济防线,因此”国家赔偿法”的适用与否便应视人民的自由、权利究竟有无因国家之公权力违法行使受有损害而定,不应再有其他的限制。因此,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之解释而言,无论是前段的「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或是后段的「怠于执行职务,致人民自由或权利受损害者亦同」,所指涉者均只有:A公权力的违法行使(后段仅是将原本包含于前段的不作为态样,加以明文例示而已)。B人民的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C二者间的因果关係。D行为人的主观归责事由。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构成要件要素。以其中的B项而言,所谓的自由或权利自係指人民受”宪法”以下之整体法秩序所保障、维护之一切自由和权利,举凡人民之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名誉、物权、准物权、无体财产权及债权等均属之。易言之,重点其实是判断人民因违法公权力行为所受损害之利益是否为整体合”宪法”秩序所保护。因而,在个案中若能确定原告受侵害之利益係位于”宪法”上之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内,则固能轻易确定原告确属自由、权利受侵害;若不然,即须探求个案中系争行政法规是否已创设人民的公权利,易言之,须探讨该法规是否有保护被害人利益之意旨。基于国家赔偿是人民权利保护的最后防线,解释该法规时便应特别著重配合”宪法”而为体系解释,最后并应注重合”宪法”律解释。总之,公权利与反射利益之区别若于国家赔偿有所适用,应仅限于用以判断人民的自由或权利有无受侵害,除此之外,别无适用。(c)”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将”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解释为公务员怠于执行对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并进一步将所谓对于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解释为该职务义务具有保护第三人利益之目的者方属之。实际上已将公务员因违法不作为而造成人民损害的情况限缩至只有当该作为义务具体创设出受损害之人民的公法上请求权时,方有”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的适用。实则,如前所述,上述要件只有论及公务员客观上须具有违法的不作为而已,而不作为之违法原则上只须以作为义务存在为已足,并不须再论及作为义务的目的。故,系争判例实係误将国家赔偿责任成立的另一构成要件-人民的自由或权利受损害-植入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从而构成对人民的国家赔偿请求权成立之不合理限制。由于可能导致法院在个案中产生一方面肯定人民之自由或权利受有损害,另一方面却又否定公务员作为义务已创设受害人民之公法上请求权的荒谬见解,该号判例侵害人民的权利保护请求益发明显。以本案为例,受诉法院肯定游艇翻覆事件之罹难者生命、身体及财产受有损害,亦即其”宪法”所保障之自由、权利受侵害,也确认行政不作为之违法性,却又在解释公务员之职务义务时否认受害者有公权利,不但矛盾,而且使”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实际上几无适用馀地。该号判例错误解释”国家赔偿法”的结果,是容认国家因不作为而损害人民时,无论伤亡有多惨重,都毋庸负责!(d)学说上有对此现象提出解释者,谓”最高法院”对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解释係借用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公务员因故意违背对于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致第三人之权利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此一见解在国家仅负代位责任的思想下,似乎言之成理。然而,今日国家责任的思潮已进入自己责任论作为指导原则的时代,在基于公平思想而儘量将公权力追求公益时所造成损害平均分担给国民全体的思考下,国家责任的范围早已藉著类似徵收侵害之补偿等责任类型的出现而大幅扩大,因此,上述在法条上并无任何依据的「借用」与时代潮流显不相符,固守其中无异故步自封。退万步言之,纵在比较法学上可知德国目前对于「公务员执行职务」的解释仍拘泥于「对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但就其学说、实务界多年来对于「第三人」的解释仍混乱甚至矛盾而言,我国实无必要对其亦步亦趋,否则不但侵害了人民的权利保护请求权,也造成”国家赔偿法”在适用上欠缺安定性和可预测性。(e)小结:综据上述,可知系争判例在诉权的具备以外,透过解释另行增加了国家赔偿请求权成立的条件,实已对于因公务员违法不作为而受有损害之人民透过国家赔偿诉讼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添加了不合理的限制,侵害了人民的权利保护请求权或广义的诉讼基本权。(三)声请人对于本案所持之立场与见解:声请人认为系争判例侵害其”宪法”上所保障之权利保护请求权(”宪法”第十六条及第二十四条),却不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所要求之要件,违反了平等原则;此外,也使”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之适用丧失了”宪法”所重视的安定性及可预测性。因此,自係违宪而应予宣告不再援用,理由如下:1系争判例违反法律保留原则:(1)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如何,固然多所争议,但于侵害人民权利事项有所适用却无疑义。”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人民之自由或权利,除为追求该条规定之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通说及实务界率皆肯定係”宪法”对基本权之限制乃法律保留事项的明白肯定。由于”宪法”直接拘束国家所有权力,因此,”宪法”第二十三条的法律保留原则不但拘束行政及立法机关,也成为依法审判原则之内涵而拘束司法机关。准此,若无法律依据或授权,司法机关超越解释活动的界限而为司法造法时侵犯人民基本权利,自已违反”宪法”第二十三条的法律保留原则。(3)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的条文用语而言,「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之字义并不限于对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或是限于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为目的之职务,因此,系争判例实已对系争规定作了目的性限缩。按,目的性限缩并非解释法律,而是对于法律中的隐藏性漏洞(verdecketRechtsluecke)依据非相类似者应为不相同处理的法理,予以填补,自已属司法造法。惟,法官的规范制订权限相对于国会而言,仅居于补充地位,其发动须以漏洞确属存在为前提,并且行使时不得逾越法律保留原则的界限。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之「违背职务」而言,如前所述,在文义上并不限于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为目的之职务,由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规定同时也是客观有效的法规范,而对位阶在”宪法”以下的所有法规范的解释适用,具有影响、指导的作用(此即基本权的扩散效力(Austrahlungswirkung)),对”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解释适用,自亦须衡诸”宪法”第十六条及第二十四条欲保障人民权利,使其有权利必有救济的规范意旨而为体系解释,准此,应认为”国家赔偿法”的目的乃在儘量填补人民因公权力违法行使所受之损害,而不应侷限于有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为目的之职务的违法执行时,方许请求国家赔偿。故”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就原始文义而言,本即不存在任何违反规范计画(Planwidrig)的漏洞,从而”最高法院”于系争判例所进行之造法活动,并无”宪法”上的正当性基础,进而,系争判例造法的结果既已限制声请人等之基本权利,造法活动自身复无”宪法”上的权限基础,也无法律的授权,自已违反了”宪法”第二十三条的法律保留原则。2系争判例违反比例原则:(1)”宪法”第二十三条所谓的「必要时」,依我国学者多数之见解,係指限制基本权之目的与限制所用手段间,须具有合理的比例关係,亦即学理上所谓的比例原则之”宪法”上依据。(2)退万步言,为避免国家赔偿请求权的成立浮滥,造成国家财政的过重负担,有必要对”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的成立予以严格解释,事实上也毋庸使用目的性限缩来限制人民诉讼权的手段为之。盖国家赔偿诉讼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诉讼有其雷同之处,即均以直接被害人为限,始得请求赔偿。至于是否为直接被害人,则属因果关係有无之客观事实认定的问题,因此,只要在事实认定上严格把关,精确界定因果关係成立之范围,即不难达成避免浮滥的目的,自然毋须于找法(Rechtsgewinnung)层次上即以司法造法的手段来侵害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请求权。就此而言,系争判例实未能慎选对人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自与比例原则有违。3系争判例违反平等原则:(1)系争判例将”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后段的职务解为对于第三人应执行之职务者始能当之,已如前述。惟,该条规定所著重者係公权力的违法行使所造成之损害填补问题,而违法行使之态样本不应区分作为或不作为,因此,无论是前段或后段之规定,基于后段实係前段之例示,在解释上即应一致而无差别。系争判例作成后,却使因公务员违法作为而受损害之人民请求国家赔偿时,较易于因不作为而受损害之人民。其间之差别待遇(discrimination)在”宪法”上并无合理之基础,而违反了平等原则。(2)”国家赔偿法”制定施行前,”最高法院”一度以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及民法第二十八条作为人民遭受公务员违法执行职务而受损害时,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的基础。查该二条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均不以受僱人或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所执行职务係对于他人应执行之职务为要素,何以反而”国家赔偿法”施行后人民求偿之限制更趋严格?如此不但有违”宪法”第二十四条所为”宪法”委託之旨,与”国家赔偿法”施行前之案件相比,其间之差别待遇亦明白可见,而此区分却亦欠缺”宪法”上理由而违反平等原则。4系争判例使”国家赔偿法”的适用丧失明确性和预测可能性:(1)德国法哲学大儒赖特布鲁(Radbruch)曾谓,法的理念有三,即法的安定性、合乎正义及合目的性,其中以法的安定性居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为使法的适用能够安定,法规范所使用的文字及解释均须明确,受规范效力所及之人方能预测法规范将如何适用,不致因法律地位或既得权益的突然变动而措手不及,遭致重大损失。易言之,法律安定性实为人民权利的法律保障之根本前提,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之”宪法”,对所有实证法规范自亦要求其具有明确性及可预测性。现行”宪法”对此虽无明文,但通说皆肯定源自法律安定性之要求的信赖保护原则及法律不溯既往原则乃”宪法”之不成文原理,故违背法律安定性之要求自仍属违宪。(2)系争判例使”国家赔偿法”于行政不作为造成人民损害之案件的适用,全繫于受诉法院对行政法规之规范目的的探求。然而,保护规范理论本身并不能就如何判断该法规有保护被害人利益之意旨提出明确标准,”最高法院”以下之各级法院及行政法院也未曾创造出明确见解,因此目前除非有完全相同之前例,否则几乎无人能预测或判断被害人究竟有无公权利。不独我国如此,保护规范理论之母国德国的审判实务亦同。公权利、法律上值得保护之利益与反射利益已成为适用时几无预测可能的超级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国家赔偿法”的适用成为受诉法院的法律感情和价值观点之游戏场所,对”宪法”所要求之安定性原则的破坏不言可喻,因而人民自无法安稳享有由”宪法”所赋予之既得权益。就此而言,系争判例违宪更属明显。(四)解决疑义必须声请解释”宪法”之理由1综据上述,”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七○四号判例违宪情形已臻明显,声请人为行使”宪法”所赋与之基本权利,并维持整体法秩序之合宪性,有必要声请解释”宪法”。2自本事件以降,近年来因政府失职致酿成重大公共安全危害之事故,被害人请求国家赔偿时,皆因系争判例作梗而致败诉。该号判例加上”最高法院”对于公权利有无之认定的保守态度,已成为人民权利保障的重大障碍,同时也使行政机关高枕无忧而不思善尽职务。因该号判例之长年适用,本案及其他相类案件的行政官员可以完全不思作为而免除国家赔偿责任,常此以往,如何冀望全方位之积极政府的产生?当此行政官员习于因循苟且之世,立法机关复懈怠有加,若司法机关不能勇于确认、保障人民”宪法”上之权利,恐怕人民不但不敢奢望政府能积极为其造福,还须祈祷现状不再恶化。去年的贺伯风灾及今年的温妮风灾,无非都是此次日月潭游艇翻覆事件的续集。若大院未能护卫”宪法”保障人民之崇高法旨,恐台湾将笃定沦为灾难之岛矣。此致“司法院”声请人:薛○宣等二十二人代理人:黄静嘉律师孙明熙律师辜郁雯律师尤伯祥律师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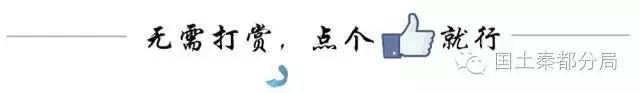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给予删除.)